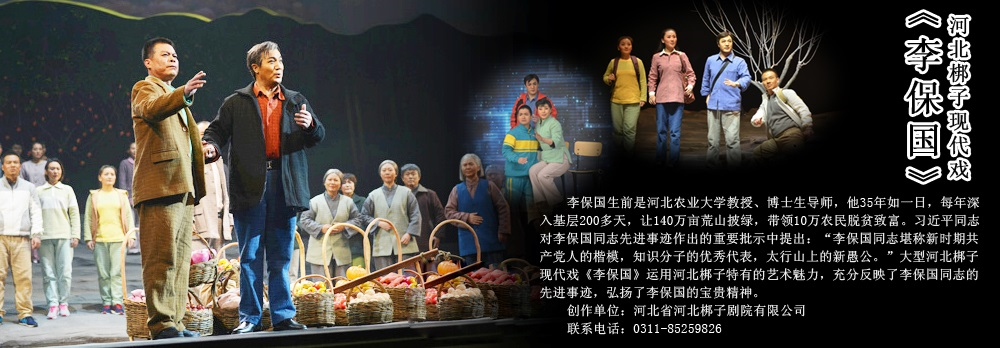关于“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新思考
责任编辑:王琳 发布日期:2021-11-12
何玉人《中国戏曲的世纪命题——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及“现代剧”的确立》一文写道:“在20世纪的中国戏剧史上,戏曲表现现代生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话题,许多人为之付出了心血和智慧。”文学艺术毕竟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如果戏曲无法反映、描写现实生活,即表现现代生活,那么终将成为一种历史的遗形物,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抛在后面。如果戏曲脱离了观众的现实生活,永远停留在“唐三千、宋八百”,那么终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被观众遗忘。然而戏曲“旧的形式”与现代生活“新的内容”之间有着种种矛盾冲突,如何使用“旧的形式”表现“新的内容”,这是亟需探讨的理论问题。
梅兰芳虽然认为京剧可以运用传统程式以及创造新程式表现现代生活,但是最终开出的药方却是“两条腿走路”,意即京剧、昆曲这样程式化程度极高的剧种,主要任务还是表现古代生活,而程式化程度不高的地方小戏更加适合表现现代生活。梅兰芳这一结论,对京剧、昆曲表现现代生活的现代戏发展之路基本上是持消极态度的。
那么,如何评价梅兰芳关于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实践与理论探索?梅兰芳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解决?例如,为何排演时装新戏、现代戏便容易沦为“话剧加唱”?为何运用传统戏的“旧形式”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内容”会枘圆凿方?难道程式化程度高的昆曲与京剧就注定成为“唐三千、宋八百”这样的文化遗产,无法表现现代生活了吗?一旦戏曲无法表现现代生活,那么便注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成为“历史的遗形物”与“博物馆的艺术”了。
一、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重要意义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妨思考,梅兰芳为什么如此关切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重要意义与迫切性在于什么?
如果我们仅仅就戏曲而论戏曲,便无法理解梅兰芳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全体知识分子的焦虑。那便是,面临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西方文明、西方文化的入侵,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传统文化将如何安身立命,又将何去何从?戏曲仅仅是华夏文明之树的一个小小枝杈,事实上,从思想到哲学,从语言到文字,再到政治制度、学术体系、社会生活,这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方方面面,都近乎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境地。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随着封建帝制的倒塌而垮掉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封建帝国,更是华夏民族的魂。
从此华夏民族成为一缕游魂,至今仍无处安放,无论是旧文人士大夫的“中体西用”还是新文化文人的“全盘西化”,似乎都无法给它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如方朝晖在《“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中所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们就是这样在学习和模仿西学的过程中一步步埋葬了自身的伟大传统,一步步摧毁了原本为任何一个中国读书人应有的信仰和价值的源头。一步步使自身的精神家园陷入于可怕的深渊,走到了今天这种穷途末路、无家可归的境地。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那么,究竟何为“现代生活”?“现代”本来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不包含民族特色,只包含时间意义的中性词。工业革命和科学精神虽起源于西方,但随之植入中国的,却是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西方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思维方式、流行文化等等。不知不觉中,“传统”等同于“农业文明”,故而“中国”等同于“旧”,“现代”等同于“工业文明”,故而“西方”等同于“新”,我们要弃旧从新、走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全盘西化,如此以偏概全、偷换概念,竟无人推敲其中的逻辑问题,即,为何农业文明在物质文明方面落后于工业文明则农业文明便一无可取之处?为何工业文明起源于西方则西方文明便全盘优于华夏文明?为何工业文明、科学精神是从西方传来的,则中国的“现代化”就需要以丢失民族性为代价?为何现代生活不可以由华夏文明中优于西方文明的部分来引领?西方的坚船利炮带来的仅仅是科学技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自毁长城般地摧毁了整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难道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的物质生活就决定了一切,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现代”与华夏文明、传统文化是从根本上龃龉的吗?总而言之,为何“现代”就等同于“西方”,为何将“新学”这顶褒义的帽子扣在“西学”之上,而将“旧学”这顶颇含贬义的帽子扣在“中学”之上?
如果我们不从根子上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戏曲表现现代生活便永远是缘木求鱼。所以,为何用传统戏的“旧形式”,无法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内容”呢?其实关键不在于“旧”与“新”的冲突,而是在于“中”与“西”的冲突,是民族化的形式与西化现代生活的内容之间的冲突。接近于全盘西化的现代生活,更加适合由西方话剧来表现,执着于用戏曲这种极具民族性的形式,来表现西化的现代生活内容,不啻于枘圆凿方、南辕北辙。
二、戏曲应当如何表现现代生活以及表现什么样的现代生活?
现代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戏曲应该表现什么样的现代生活?戏曲应当如何表现现代生活?是戏曲表现现代生活还是现代生活学习戏曲?
若要回答这些问题,便不能不回到梅兰芳所提出的“体系”。梅兰芳曾多次明确提出“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这一提法,无疑是高瞻远瞩的。
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文明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中国的现代生活有着全盘西化的倾向,从形而上的学术体系、政治制度、思维方式,到形而下的物质文化,都曾经有着摒弃自己民族特色的倾向,如果说,一个民族从硬件到软件都被颠覆,那么这个民族离亡族灭种、沦为行尸走肉还有多远?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固然是大势所趋,但我们更加需要关心的是,“现代”等同于“西化”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吗?
如果我们不解决“现代生活”与“华夏文明”“传统文化”在根本上的龃龉,则戏曲的发展将永远面临困境,戏曲是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之树的枝杈,若表现与华夏文明、传统文化南辕北辙的“现代生活”,则不啻于自我毁灭,若坚守自我,则势必失去现实土壤,成为“历史的遗形物”“博物馆的艺术”。
所以,戏曲革新的根本应当是华夏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革新,是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在重科学重技术的学术思潮之下,五千年华夏文明、传统文化如何去芜存菁的问题。笔者以为,无论是戏曲改革还是文化改革,根本都在于坚守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仅是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更是整个华夏文明体系,是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它是下学上达、彻上彻下的,自形而上的“道”(哲学思想、思维方式)至形而下的“器”(表现手法、表现形式),都是自成一体的。
换言之,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是华夏文明体系、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之内的,坚守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关键在于坚守华夏文明体系。华夏文明体系一旦被破坏,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又将何去何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因此,唯有建立体系思维才能够明白,为何时装新戏存在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冲突,如果传统戏的形式是华夏文明体系之内的,而所谓的“现代生活”是华夏文明体系之外的,那么,华夏文明体系之内的传统戏形式便无法表现华夏文明体系之外的“现代生活”内容。而一旦表现华夏文明体系之外的“现代生活”,便必然如梅兰芳所言脱离中国戏曲表演体系。
也就是说,无论是华夏文明、传统文化还是戏曲,任何革新都应当在体系之内。可以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心态会通西学,吸收借鉴西方文明、西方戏剧的优长,但不能脱离自身的体系。
关键正在于两点,其一是不能将戏曲表演实践放在“西学”体系之内。其二是不能将戏曲表演理论放在“西学”体系之内。
那么,这个“体系”的精髓究竟是什么?
农业社会,儒家思想与宗法制是与当时经济基础相匹配的上层建筑,也是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道统”,而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变,使儒家思想与宗法制不再适应经济基础,故而“礼崩乐坏”,学术领域则引入西方近现代科学体系,从而全面放弃了以“六艺”为核心,以经、史、子、集为框架;以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中学”体系。然而华夏文明核心的哲学思想与思维方式是不会变的,例如“天人合一”“易”“太极”“阴阳五行”等。
从这个角度而言,为何时装新戏便容易脱离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我们先从传统戏表现的古代生活,以及时装新戏表现的现代生活谈起。
如梅兰芳所言,传统戏从穿扮到身段、唱腔、伴奏、布景都是自成体系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戏所表现的古代生活,便是统御在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的核心哲学美学思想之下的,如上一章所论的“天人合一”“易”“太极”“阴阳五行”等。中国传统社会礼乐刑政各个方面:典章、制度、建筑、器具、服装、音乐、礼仪、习俗等等,无不涵摄在先王对于天地万物之道的体察之中。这些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分而言之,则为万殊,合而言之,则为一体。本是一体之朗现,一心之遍润,发而为乐律,则为宫商角徵羽之和睦;发而为人事,则为仁义礼智信之融洽;发而为仪礼,则为吉凶军宾嘉之雍容;发而为度数,则为规矩绳权衡之允谐……传统社会生活合于规矩度数的各个方面,经过高度凝炼之后,在戏曲之中展现,便成了我们所说的行当程式系统。在戏曲中,格律有平上去入之抑扬,乐律有黄钟大吕之铿锵,行当有生旦净末丑之俨然,程式系统则有“周旋中轨,折旋中矩”之森然。舞台上的身段“比象天地”,故而如梅兰芳所言,戏曲身段都是“曲线”的,应天体运行轨迹之“圆”,即便是剧场建筑也有着“比象天地”的色彩,如圆的藻井与方的舞台,蕴含着天圆地方的思想(天并非为圆,但天体运行轨迹无疑是圆的,在这一意义上,称“天圆”并无不妥)。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统摄在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体系之内的,而表现古代生活的传统戏,其舞台上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因统摄在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体系之内,故而亦自成体系。
而时装新戏表现的现代生活,首先在思想上便有了脱离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体系的倾向,体现在具体生活之中,如建筑、服装、器具这些形而下的事物,也都脱离了原本的体系。那么,在戏曲舞台上,最能体现体系之别的,便是服装穿扮。
时装新戏,顾名思义是穿时装表演现代生活的改良京剧。笔者在此以服装穿扮为例,分析时装新戏何以脱离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体系及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原因。
正如《礼记·深衣》所言:“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a无论传统戏服还是古装戏服,都是在传统服饰体系之内的。传统服饰的方方面面都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高度体现,它强调“天人合一”“比象天地”,因此,“袂圜袷方”如“规矩”以应圆与方,“下齐”如“权衡”以应平,“负绳”以应直。传统服饰的前后中缝为“负绳”,正对应人体的中缝,在引导人体的“气”的运行的同时,将正直之意蕴含其中;而下摆平直如同“权衡”,其中寄托着公平之意;袂圆契合宇宙运行的规律——天体运行的规律便是“圆”的。这也便是为什么戏曲中的所有动作都是“曲线”,一旦穿上戏服,自然而然想走台步、走圆场。这种“比象天地”的传统服饰,能够辅助人们端正姿势,因此穿上戏服,不知不觉中,一举一动便不偏不倚、平和中正了,“周旋中轨,折旋中矩”,举手投足自然而然呼应天地大道。这其实是十分科学的,例如现代西服的下摆经常有剪裁不平的设计,而中国传统服饰的下摆则永远是平的,穿上这种横平竖直的服饰,人体自然而然行得正坐得直,行动也自然有矩矱仪轨,因为倘若行不正坐不直,服装自然就不平正、不美观了,而立体剪裁、不规则剪裁的西服恐无此效果。这便如梅兰芳所言:“京剧的表演艺术,如唱腔、音乐、身段、动作,与宽大的行头、脸谱、长胡子、水袖、厚底靴、马鞭、船桨等等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是自成体系的。”
而时装(尤其是西服革履)本身便是属于另一个文明体系的,与华夏文明体系格格不入。西服中的立体剪裁如腰省、胸省、垫肩、拉链、不规则下摆等,处处体现的是征服、割裂、对立的思想,穿上西服,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举手投足直来直去,不再符合“太极”之道,自然与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不相契合了。这也便是穿时装演京剧为何容易脱离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原因了,因为西服革履在形而上的哲学美学观念与思维方式上,便是与传统戏的身段格格不入的。两者完全是属于两个体系的事物,无法强行捏合在一起。
所以在戏曲革新与发展之中,戏曲史的维度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何时,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但并不是唯一的维度。不能因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就不加批判地接受和提倡,好比一个人真的犯了错误,也是错误。所以,并不能因为梅兰芳在历史上排演过时装新戏,就认为时装新戏这条路是正确的。较之历史的维度,更加重要的维度应当是华夏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维度,只有符合这个维度,才是传承了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梅兰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思了时装新戏及现代戏,他认为时装新戏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脱离了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而笔者认为,时装新戏不仅脱离了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更重要的是脱离了华夏文明体系。
在民国初年,梅兰芳走上了两条戏曲革新之路,一条是时装新戏,一条是古装新戏,然而事实证明只有古装新戏这条路是走得通的。那便是因为时装新戏不契合于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的精神,从而脱离了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而其根本原因在于时装新戏所表现的现代生活——例如时装乃至现代社会全盘西化的生活方式,其本身所蕴含的哲学美学观念、思维方式,便脱离了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的体系。而古装新戏契合于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的精神,坚守了中国戏曲表演体系。
刘汭屿《梅兰芳古装歌舞剧的古典美学建构》一文中指出了梅兰芳古装新戏在三个方面进行的古典美学建构,其一是古装造型,其二是古典舞蹈,其三是古典文学与意境。这三个方面是梅兰芳古装新戏的“移步”,是对京剧传统戏的大幅度革新。京剧传统戏的青衣扮相是穿帔、梳大头的,其服装——帔与褶子,主要以宋代褙子与明代披风为原型(衣掩裙),而梅兰芳古装新戏(以《嫦娥奔月》为例)的造型则参考了古代仕女图,其服装是以古代襦裙为原型的(裙掩衣),体现出婀娜多姿、飘飘欲仙的效果。传统戏的青衣梳大头,而梅兰芳古装新戏(以《嫦娥奔月》为例)的发式则是根据古画中的仕女形象设计的“吕”字形高髻。
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如此描写:“(一)服装:上穿淡红色的软绸对胸短袄,下系白色软绸长裙。袄子上加绣了花边,裙子系在袄子外面。老戏的服装,总是短裙系在袄子里边。这一点是很显著的不同。腰里围的丝绦,上面编成各种的花纹,还有一条丝带,垂在中间。带上还打一个如意结,两旁垂着些玉佩。(二)头面:头上正面梳两个髻,上下叠着成‘吕’字形,右边用一根长长的玉钗,斜插入上面那个髻里,钗头还挂有珠穗,左边再戴一朵翠花。”
梅兰芳古装新戏的演出效果是极为成功的,当他初演《嫦娥奔月》,第一次穿着新设计的古装在观众面前亮相的时候,台下的观众来回打量着他的造型,全场静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完全被这飘飘欲仙的古装造型吸引了。而古装新戏中的古典舞蹈、古典文学意境亦是对京剧老戏传统的极大突破,众所周知京剧传统戏中,青衣重唱不重做,往往是抱着肚子唱,而京剧传统戏的唱词也较为俚俗。由此可见,梅兰芳京剧革新的步子迈得不可谓不大,但为何这种革新是成功的呢?主要在于无论是古装造型、还是古典歌舞、古典文学意境,都是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体系内部的革新。无论是衣掩裙的褶子,还是裙掩衣的古装,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是在华夏衣冠体系之内的,契合于华夏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古典哲学、美学观念与思维方式的体现。古装新戏中的古典舞蹈、古典文学意境亦然。由此可见,梅兰芳戏曲革新思想是不拘一格的,然而不拘一格的前提条件即在于守住体系。这个体系,从小的方面而言是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从大的方面而言是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的体系,也即传统哲学美学观念与思维方式(道)与传统形式(器)彻上彻下一体的体系。只要在这个体系之内,任何革新都是可以接受的。相反脱离了这个体系,则任何革新都可能使得内容与形式格格不入。
梅兰芳作为一名传统的京剧演员,他的身上传承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戏曲的血脉,更是五千年华夏文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因此他对“体系”是十分敏感的,虽也曾经排演时装新戏,用体系之外的新手法、新形式(西方手法、西方形式)表现体系之外的,全盘西化的现代生活,但最终却归于体系,得出结论——京剧并不是最适合表现现代生活的,京剧的主要任务还是在于表演历史题材,即表现古代生活。故而梅兰芳在建国之后排演的新戏并不是时装新戏、现代戏,甚至也不是古装新戏,而是由同名豫剧移植而来的《穆桂英挂帅》,如梅兰芳所言是“穿老戏服装的新戏”,相当于还是走传统戏的路子。
如果现代生活从形而上的思想到形而下的形式,都已经脱离了华夏文明的体系,先不论戏曲,先论我们所谓的现代生活,如果脱离了历史所形成的民族心理特点,丧失了本民族的根本特性,即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色,那么现代生活的“新内容”自然与传统戏曲的“旧形式”格格不入,这并不是“新”与“旧”的格格不入,而是“中”与“西”的格格不入。所以,与其说戏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毋宁说戏曲是我们每个华夏儿女的乡愁。与其说戏曲应当表现现代生活,毋宁说现代生活应当学习戏曲。
工业化、信息化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两千年的儒家道统固然已经不适合当今社会,然而华夏文明体系的精髓,如整体性、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分明是优于西方文明的。如何在坚持华夏文明体系精髓的基础上统御工业化的物质文明,统御西方近现代科学,建立民族化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走民族化的现代之路,这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结 语
总而言之,戏曲确实应当表现现代生活,否则便会脱离观众的现实生活,从而成为历史的遗形物。但是,现代生活未必一定是西化的生活,从形而上的哲学思想(道)到形而下的生活方式(器),都不必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我们应当创造民族性的现代生活,而非破坏传统戏曲中民族性的美学原则,如程式化、虚拟性、写意型等,破坏传统戏曲中民族化的形式,如四功五法等,以适应西方化的现代生活。如上文所论,传统社会生活从形而上的道到形而下的器都是一体的,是华夏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传统戏曲表演体系从形而上的美学原则、本体规律到形而下的形式,也是彻上彻下一体的。而创造民族性的现代生活,则包括自形上至形下的方方面面,从形而上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到形而下的社会生活,都需要在体系之内进行改革。一旦建立体系,则本立而道生,动作有揖让进退之从容,音律有平上去入之抑扬,上至思想,下至形式,皆一以贯之,则又何愁戏曲无法表现现代生活呢?
责编:吴敏
作者:中央戏剧学院 庞婧绮 来源: 文旅中国
梅兰芳虽然认为京剧可以运用传统程式以及创造新程式表现现代生活,但是最终开出的药方却是“两条腿走路”,意即京剧、昆曲这样程式化程度极高的剧种,主要任务还是表现古代生活,而程式化程度不高的地方小戏更加适合表现现代生活。梅兰芳这一结论,对京剧、昆曲表现现代生活的现代戏发展之路基本上是持消极态度的。
那么,如何评价梅兰芳关于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实践与理论探索?梅兰芳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解决?例如,为何排演时装新戏、现代戏便容易沦为“话剧加唱”?为何运用传统戏的“旧形式”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内容”会枘圆凿方?难道程式化程度高的昆曲与京剧就注定成为“唐三千、宋八百”这样的文化遗产,无法表现现代生活了吗?一旦戏曲无法表现现代生活,那么便注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成为“历史的遗形物”与“博物馆的艺术”了。
一、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重要意义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妨思考,梅兰芳为什么如此关切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重要意义与迫切性在于什么?
如果我们仅仅就戏曲而论戏曲,便无法理解梅兰芳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全体知识分子的焦虑。那便是,面临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西方文明、西方文化的入侵,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传统文化将如何安身立命,又将何去何从?戏曲仅仅是华夏文明之树的一个小小枝杈,事实上,从思想到哲学,从语言到文字,再到政治制度、学术体系、社会生活,这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方方面面,都近乎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境地。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随着封建帝制的倒塌而垮掉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封建帝国,更是华夏民族的魂。
从此华夏民族成为一缕游魂,至今仍无处安放,无论是旧文人士大夫的“中体西用”还是新文化文人的“全盘西化”,似乎都无法给它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如方朝晖在《“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中所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们就是这样在学习和模仿西学的过程中一步步埋葬了自身的伟大传统,一步步摧毁了原本为任何一个中国读书人应有的信仰和价值的源头。一步步使自身的精神家园陷入于可怕的深渊,走到了今天这种穷途末路、无家可归的境地。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那么,究竟何为“现代生活”?“现代”本来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不包含民族特色,只包含时间意义的中性词。工业革命和科学精神虽起源于西方,但随之植入中国的,却是西方文明的方方面面,包括西方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思维方式、流行文化等等。不知不觉中,“传统”等同于“农业文明”,故而“中国”等同于“旧”,“现代”等同于“工业文明”,故而“西方”等同于“新”,我们要弃旧从新、走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全盘西化,如此以偏概全、偷换概念,竟无人推敲其中的逻辑问题,即,为何农业文明在物质文明方面落后于工业文明则农业文明便一无可取之处?为何工业文明起源于西方则西方文明便全盘优于华夏文明?为何工业文明、科学精神是从西方传来的,则中国的“现代化”就需要以丢失民族性为代价?为何现代生活不可以由华夏文明中优于西方文明的部分来引领?西方的坚船利炮带来的仅仅是科学技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自毁长城般地摧毁了整个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难道先进的科学技术、丰富的物质生活就决定了一切,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现代”与华夏文明、传统文化是从根本上龃龉的吗?总而言之,为何“现代”就等同于“西方”,为何将“新学”这顶褒义的帽子扣在“西学”之上,而将“旧学”这顶颇含贬义的帽子扣在“中学”之上?
如果我们不从根子上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戏曲表现现代生活便永远是缘木求鱼。所以,为何用传统戏的“旧形式”,无法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内容”呢?其实关键不在于“旧”与“新”的冲突,而是在于“中”与“西”的冲突,是民族化的形式与西化现代生活的内容之间的冲突。接近于全盘西化的现代生活,更加适合由西方话剧来表现,执着于用戏曲这种极具民族性的形式,来表现西化的现代生活内容,不啻于枘圆凿方、南辕北辙。
二、戏曲应当如何表现现代生活以及表现什么样的现代生活?
现代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戏曲应该表现什么样的现代生活?戏曲应当如何表现现代生活?是戏曲表现现代生活还是现代生活学习戏曲?
若要回答这些问题,便不能不回到梅兰芳所提出的“体系”。梅兰芳曾多次明确提出“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这一提法,无疑是高瞻远瞩的。
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文明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中国的现代生活有着全盘西化的倾向,从形而上的学术体系、政治制度、思维方式,到形而下的物质文化,都曾经有着摒弃自己民族特色的倾向,如果说,一个民族从硬件到软件都被颠覆,那么这个民族离亡族灭种、沦为行尸走肉还有多远?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固然是大势所趋,但我们更加需要关心的是,“现代”等同于“西化”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吗?
如果我们不解决“现代生活”与“华夏文明”“传统文化”在根本上的龃龉,则戏曲的发展将永远面临困境,戏曲是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之树的枝杈,若表现与华夏文明、传统文化南辕北辙的“现代生活”,则不啻于自我毁灭,若坚守自我,则势必失去现实土壤,成为“历史的遗形物”“博物馆的艺术”。
所以,戏曲革新的根本应当是华夏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革新,是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之下,在重科学重技术的学术思潮之下,五千年华夏文明、传统文化如何去芜存菁的问题。笔者以为,无论是戏曲改革还是文化改革,根本都在于坚守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仅是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更是整个华夏文明体系,是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它是下学上达、彻上彻下的,自形而上的“道”(哲学思想、思维方式)至形而下的“器”(表现手法、表现形式),都是自成一体的。
换言之,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是华夏文明体系、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之内的,坚守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关键在于坚守华夏文明体系。华夏文明体系一旦被破坏,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又将何去何从?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因此,唯有建立体系思维才能够明白,为何时装新戏存在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冲突,如果传统戏的形式是华夏文明体系之内的,而所谓的“现代生活”是华夏文明体系之外的,那么,华夏文明体系之内的传统戏形式便无法表现华夏文明体系之外的“现代生活”内容。而一旦表现华夏文明体系之外的“现代生活”,便必然如梅兰芳所言脱离中国戏曲表演体系。
也就是说,无论是华夏文明、传统文化还是戏曲,任何革新都应当在体系之内。可以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心态会通西学,吸收借鉴西方文明、西方戏剧的优长,但不能脱离自身的体系。
关键正在于两点,其一是不能将戏曲表演实践放在“西学”体系之内。其二是不能将戏曲表演理论放在“西学”体系之内。
那么,这个“体系”的精髓究竟是什么?
农业社会,儒家思想与宗法制是与当时经济基础相匹配的上层建筑,也是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道统”,而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变,使儒家思想与宗法制不再适应经济基础,故而“礼崩乐坏”,学术领域则引入西方近现代科学体系,从而全面放弃了以“六艺”为核心,以经、史、子、集为框架;以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中学”体系。然而华夏文明核心的哲学思想与思维方式是不会变的,例如“天人合一”“易”“太极”“阴阳五行”等。
从这个角度而言,为何时装新戏便容易脱离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我们先从传统戏表现的古代生活,以及时装新戏表现的现代生活谈起。
如梅兰芳所言,传统戏从穿扮到身段、唱腔、伴奏、布景都是自成体系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传统戏所表现的古代生活,便是统御在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的核心哲学美学思想之下的,如上一章所论的“天人合一”“易”“太极”“阴阳五行”等。中国传统社会礼乐刑政各个方面:典章、制度、建筑、器具、服装、音乐、礼仪、习俗等等,无不涵摄在先王对于天地万物之道的体察之中。这些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分而言之,则为万殊,合而言之,则为一体。本是一体之朗现,一心之遍润,发而为乐律,则为宫商角徵羽之和睦;发而为人事,则为仁义礼智信之融洽;发而为仪礼,则为吉凶军宾嘉之雍容;发而为度数,则为规矩绳权衡之允谐……传统社会生活合于规矩度数的各个方面,经过高度凝炼之后,在戏曲之中展现,便成了我们所说的行当程式系统。在戏曲中,格律有平上去入之抑扬,乐律有黄钟大吕之铿锵,行当有生旦净末丑之俨然,程式系统则有“周旋中轨,折旋中矩”之森然。舞台上的身段“比象天地”,故而如梅兰芳所言,戏曲身段都是“曲线”的,应天体运行轨迹之“圆”,即便是剧场建筑也有着“比象天地”的色彩,如圆的藻井与方的舞台,蕴含着天圆地方的思想(天并非为圆,但天体运行轨迹无疑是圆的,在这一意义上,称“天圆”并无不妥)。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统摄在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体系之内的,而表现古代生活的传统戏,其舞台上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因统摄在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体系之内,故而亦自成体系。
而时装新戏表现的现代生活,首先在思想上便有了脱离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体系的倾向,体现在具体生活之中,如建筑、服装、器具这些形而下的事物,也都脱离了原本的体系。那么,在戏曲舞台上,最能体现体系之别的,便是服装穿扮。
时装新戏,顾名思义是穿时装表演现代生活的改良京剧。笔者在此以服装穿扮为例,分析时装新戏何以脱离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体系及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原因。
正如《礼记·深衣》所言:“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a无论传统戏服还是古装戏服,都是在传统服饰体系之内的。传统服饰的方方面面都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高度体现,它强调“天人合一”“比象天地”,因此,“袂圜袷方”如“规矩”以应圆与方,“下齐”如“权衡”以应平,“负绳”以应直。传统服饰的前后中缝为“负绳”,正对应人体的中缝,在引导人体的“气”的运行的同时,将正直之意蕴含其中;而下摆平直如同“权衡”,其中寄托着公平之意;袂圆契合宇宙运行的规律——天体运行的规律便是“圆”的。这也便是为什么戏曲中的所有动作都是“曲线”,一旦穿上戏服,自然而然想走台步、走圆场。这种“比象天地”的传统服饰,能够辅助人们端正姿势,因此穿上戏服,不知不觉中,一举一动便不偏不倚、平和中正了,“周旋中轨,折旋中矩”,举手投足自然而然呼应天地大道。这其实是十分科学的,例如现代西服的下摆经常有剪裁不平的设计,而中国传统服饰的下摆则永远是平的,穿上这种横平竖直的服饰,人体自然而然行得正坐得直,行动也自然有矩矱仪轨,因为倘若行不正坐不直,服装自然就不平正、不美观了,而立体剪裁、不规则剪裁的西服恐无此效果。这便如梅兰芳所言:“京剧的表演艺术,如唱腔、音乐、身段、动作,与宽大的行头、脸谱、长胡子、水袖、厚底靴、马鞭、船桨等等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是自成体系的。”
而时装(尤其是西服革履)本身便是属于另一个文明体系的,与华夏文明体系格格不入。西服中的立体剪裁如腰省、胸省、垫肩、拉链、不规则下摆等,处处体现的是征服、割裂、对立的思想,穿上西服,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举手投足直来直去,不再符合“太极”之道,自然与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不相契合了。这也便是穿时装演京剧为何容易脱离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原因了,因为西服革履在形而上的哲学美学观念与思维方式上,便是与传统戏的身段格格不入的。两者完全是属于两个体系的事物,无法强行捏合在一起。
所以在戏曲革新与发展之中,戏曲史的维度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何时,历史都是非常重要的维度,但并不是唯一的维度。不能因为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就不加批判地接受和提倡,好比一个人真的犯了错误,也是错误。所以,并不能因为梅兰芳在历史上排演过时装新戏,就认为时装新戏这条路是正确的。较之历史的维度,更加重要的维度应当是华夏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维度,只有符合这个维度,才是传承了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梅兰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反思了时装新戏及现代戏,他认为时装新戏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脱离了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而笔者认为,时装新戏不仅脱离了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更重要的是脱离了华夏文明体系。
在民国初年,梅兰芳走上了两条戏曲革新之路,一条是时装新戏,一条是古装新戏,然而事实证明只有古装新戏这条路是走得通的。那便是因为时装新戏不契合于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的精神,从而脱离了中国戏曲表演体系,而其根本原因在于时装新戏所表现的现代生活——例如时装乃至现代社会全盘西化的生活方式,其本身所蕴含的哲学美学观念、思维方式,便脱离了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的体系。而古装新戏契合于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的精神,坚守了中国戏曲表演体系。
刘汭屿《梅兰芳古装歌舞剧的古典美学建构》一文中指出了梅兰芳古装新戏在三个方面进行的古典美学建构,其一是古装造型,其二是古典舞蹈,其三是古典文学与意境。这三个方面是梅兰芳古装新戏的“移步”,是对京剧传统戏的大幅度革新。京剧传统戏的青衣扮相是穿帔、梳大头的,其服装——帔与褶子,主要以宋代褙子与明代披风为原型(衣掩裙),而梅兰芳古装新戏(以《嫦娥奔月》为例)的造型则参考了古代仕女图,其服装是以古代襦裙为原型的(裙掩衣),体现出婀娜多姿、飘飘欲仙的效果。传统戏的青衣梳大头,而梅兰芳古装新戏(以《嫦娥奔月》为例)的发式则是根据古画中的仕女形象设计的“吕”字形高髻。
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如此描写:“(一)服装:上穿淡红色的软绸对胸短袄,下系白色软绸长裙。袄子上加绣了花边,裙子系在袄子外面。老戏的服装,总是短裙系在袄子里边。这一点是很显著的不同。腰里围的丝绦,上面编成各种的花纹,还有一条丝带,垂在中间。带上还打一个如意结,两旁垂着些玉佩。(二)头面:头上正面梳两个髻,上下叠着成‘吕’字形,右边用一根长长的玉钗,斜插入上面那个髻里,钗头还挂有珠穗,左边再戴一朵翠花。”
梅兰芳古装新戏的演出效果是极为成功的,当他初演《嫦娥奔月》,第一次穿着新设计的古装在观众面前亮相的时候,台下的观众来回打量着他的造型,全场静到一点声音都没有,完全被这飘飘欲仙的古装造型吸引了。而古装新戏中的古典舞蹈、古典文学意境亦是对京剧老戏传统的极大突破,众所周知京剧传统戏中,青衣重唱不重做,往往是抱着肚子唱,而京剧传统戏的唱词也较为俚俗。由此可见,梅兰芳京剧革新的步子迈得不可谓不大,但为何这种革新是成功的呢?主要在于无论是古装造型、还是古典歌舞、古典文学意境,都是华夏文明、传统文化体系内部的革新。无论是衣掩裙的褶子,还是裙掩衣的古装,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是在华夏衣冠体系之内的,契合于华夏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古典哲学、美学观念与思维方式的体现。古装新戏中的古典舞蹈、古典文学意境亦然。由此可见,梅兰芳戏曲革新思想是不拘一格的,然而不拘一格的前提条件即在于守住体系。这个体系,从小的方面而言是中国戏曲表演体系,从大的方面而言是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的体系,也即传统哲学美学观念与思维方式(道)与传统形式(器)彻上彻下一体的体系。只要在这个体系之内,任何革新都是可以接受的。相反脱离了这个体系,则任何革新都可能使得内容与形式格格不入。
梅兰芳作为一名传统的京剧演员,他的身上传承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戏曲的血脉,更是五千年华夏文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因此他对“体系”是十分敏感的,虽也曾经排演时装新戏,用体系之外的新手法、新形式(西方手法、西方形式)表现体系之外的,全盘西化的现代生活,但最终却归于体系,得出结论——京剧并不是最适合表现现代生活的,京剧的主要任务还是在于表演历史题材,即表现古代生活。故而梅兰芳在建国之后排演的新戏并不是时装新戏、现代戏,甚至也不是古装新戏,而是由同名豫剧移植而来的《穆桂英挂帅》,如梅兰芳所言是“穿老戏服装的新戏”,相当于还是走传统戏的路子。
如果现代生活从形而上的思想到形而下的形式,都已经脱离了华夏文明的体系,先不论戏曲,先论我们所谓的现代生活,如果脱离了历史所形成的民族心理特点,丧失了本民族的根本特性,即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色,那么现代生活的“新内容”自然与传统戏曲的“旧形式”格格不入,这并不是“新”与“旧”的格格不入,而是“中”与“西”的格格不入。所以,与其说戏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毋宁说戏曲是我们每个华夏儿女的乡愁。与其说戏曲应当表现现代生活,毋宁说现代生活应当学习戏曲。
工业化、信息化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两千年的儒家道统固然已经不适合当今社会,然而华夏文明体系的精髓,如整体性、综合性的思维方式,分明是优于西方文明的。如何在坚持华夏文明体系精髓的基础上统御工业化的物质文明,统御西方近现代科学,建立民族化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走民族化的现代之路,这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结 语
总而言之,戏曲确实应当表现现代生活,否则便会脱离观众的现实生活,从而成为历史的遗形物。但是,现代生活未必一定是西化的生活,从形而上的哲学思想(道)到形而下的生活方式(器),都不必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我们应当创造民族性的现代生活,而非破坏传统戏曲中民族性的美学原则,如程式化、虚拟性、写意型等,破坏传统戏曲中民族化的形式,如四功五法等,以适应西方化的现代生活。如上文所论,传统社会生活从形而上的道到形而下的器都是一体的,是华夏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传统戏曲表演体系从形而上的美学原则、本体规律到形而下的形式,也是彻上彻下一体的。而创造民族性的现代生活,则包括自形上至形下的方方面面,从形而上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到形而下的社会生活,都需要在体系之内进行改革。一旦建立体系,则本立而道生,动作有揖让进退之从容,音律有平上去入之抑扬,上至思想,下至形式,皆一以贯之,则又何愁戏曲无法表现现代生活呢?
责编:吴敏
作者:中央戏剧学院 庞婧绮 来源: 文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