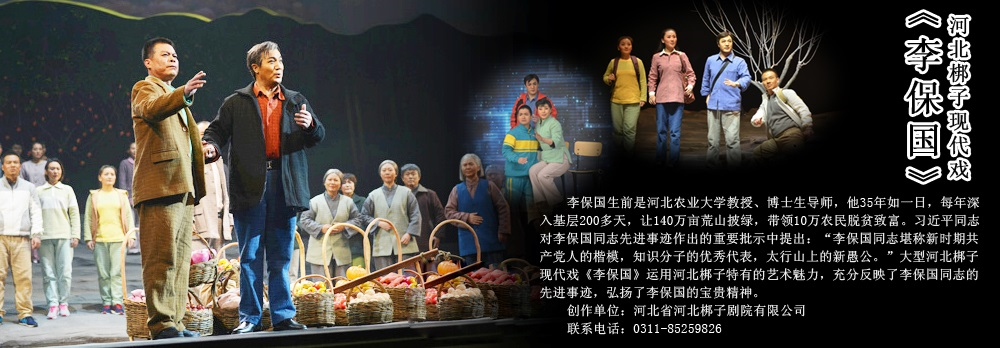戏剧,将沉浸到哪里?
责任编辑:王琳 发布日期:2023-02-16
本报记者 罗 群
戏剧演出应该是什么样的?台上声台行表、全情投入,台下鸦雀无声、正襟危坐,大概是多数人印象中的情形。而观众“质问”演员、将演员问得“张口结舌、变了脸色”,这种场面大约会令人想到演出事故,但对于一些沉浸式戏剧来说,这正是新鲜的玩法、不同的体验。
从经典之作《无人入眠》到新秀《疯狂理发店》《阿波罗尼亚》等,各类沉浸式戏剧你方唱罢我登场。近年来,沉浸式戏剧在国内演出市场上大量涌现,受到许多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其发展态势堪用如火如荼来形容。随着不同艺术门类、文娱方式的对话交流,越来越多带有戏剧元素的演艺项目加入沉浸的行列,丰富甚至挑战着传统的戏剧观念和演艺格局,也再次唤起人们对戏剧性、文学性的思考,成为令人瞩目的行业现象和文化景观。
从观看到参与,方兴未艾
尽管沉浸式戏剧有着较为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创作实绩,然而究竟什么是沉浸式戏剧?
沉浸式戏剧以新颖的演出形式、新鲜的观看体验成为市场的新晋宠儿,实际上,沉浸式戏剧并不很年轻,其历史已有数十年之久。资料显示,1975年,设计师尤金·李把一座剧场改建成游艺场,场内不仅有演出,还设有游戏机、小吃摊位、照相馆等,观众可以自由漫步,自行决定观看哪个演出,或者吃些小吃、喝点啤酒——这就是美国演艺项目《冷酷大教堂》,其艺术影响力延续至今。
多年来,为了给观众提供新鲜感、沉浸感,国内创作者想出了许多办法突破原有的演出模式,刷新戏剧的观演方式。以《奋不顾身的爱情》为代表,一些小剧场话剧虽然仍在传统的镜框式舞台上演出,但演员会配合剧情发展而在某些时刻来到观众席中表演,拉近剧情与观众的距离;以赖声川执导的话剧《如梦之梦》为代表的一批作品使用环绕式舞台或者将表演区域延伸到观众席中,沉浸感进一步增强;各大旅游景区的文旅演艺剧经常把舞台设置在真实的山水园林之间,戏剧环境与更广阔复杂的自然、人文环境相融合;被誉为沉浸式戏剧天花板的《无人入眠》在其演出场地设置了几十个房间、同时上演着不同的剧情,观众可以自行选择房间来观看,还有机会与演员互动。这些演出形式各不相同,但都笼统地冠以“沉浸”之名。
尽管沉浸式戏剧有着较为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创作实绩,然而究竟什么是沉浸式戏剧,从业者、理论界往往莫衷一是。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者阿诺德·阿隆森提出的一个比较简单、通用的定义,基本能够囊括各种看法之间的共识,即“沉浸式戏剧是一个参与性的演出事件,包括一个包罗万象的吸纳性环境,调动了所有的感觉”。以此观之,目前一部分被称为沉浸式戏剧的作品、演艺项目实际上并不十分沉浸,而更像是特殊场域展演,或处于特殊场域展演与沉浸式戏剧的中间地带。
有的在徘徊,有的很激进,不乏创作者步子迈得很大,在作品中尽可能调动多重感官并且大量“留白”,呼唤观众参与。自2017年起从英国引进、经本土化改编后落地上海的《玩味探险家》《玩味放映厅》等“玩味”系列剧集定位为赏味环境剧,将戏剧与饮食结合起来,观众不仅可以观剧、即兴互动,还能同时大快朵颐,不少观众表示很好玩、很好吃。不过,这究竟是戏剧还是真人互动游戏?许多观众在沉浸过后收获了轻松愉悦,未必会考虑这个问题。作为观众,也的确没有回答这一问题的义务。
此剧场已非彼剧场
那些呼唤观众深度参与的戏剧作品,究竟是戏剧还是真人互动游戏?
《玩味探险家》总制作人谢已在采访中表示,沉浸式戏剧“最本质的要求”就是要做一个足够新鲜、吸引人的东西,一种观众在网上无法体验的东西,于是给观众一个走出家门、来到现场的理由。
这种观点是在线上与线下、戏剧与其他相互竞争的语境中看待沉浸式戏剧的。的确,沉浸式戏剧的走红与新兴媒体的影响、文化消费方式的变革升级、激烈的市场竞争等密切相关。在注意力经济的背景下,许多曾经相隔甚远的文娱品种,一下子成了彼此的竞品,相互之间的切磋、借鉴、共融自然而然地发生。正如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韩生所说,交叉融合、边界模糊是当今艺术的共同特点,其背后是整体文化生态的沿革,源自当今社会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的深刻转型。当代观众能够轻松便捷地通过多种媒介形式获取不同的文化娱乐享受,新媒体、新技术也催生了全新的消费场景、消费体验,高速移动互联网、智能穿戴设备等的普及,还将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垂直分众的供给、丰富多元的选择大幅提升了人们在文化消费中的自主性、能动性,观众对戏剧的审美期待、戏剧人的创作方式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改变。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教师韦哲宇分析,寻求消费市场的戏剧创作者一方面引入各类景观,通过演出场域的技术、装置等为观众呈现银幕、屏幕所难以提供的精致影像和奇观;另一方面,当代戏剧也在创作和演出中鼓励游戏,让观众尽可能获得即兴、自由、创造性等在其他渠道较少享受到的差异化消费体验。不难发现,上述两种诉求在沉浸式戏剧创作演出中交相辉映,戏剧成为“幻觉机器”,让观众暂时进入虚构时空、抽离自身的社会属性,在一场戏的时间里成为某位他者,这既是体验,也是表演。表演的冲动堪称人类自古以来便具有的精神文化需求甚或一种天性,在不同社会、时代条件下被以不同的方式满足,眼下沉浸式戏剧的火爆,正是一种天性解放,恰逢其时。
某事物的蓬勃发展除了外部环境的刺激,也必定有内生动力的推动。沉浸式戏剧是戏剧人对日益挑剔的演出市场做出的积极回应,也是戏剧自身在特定条件下不断求新求变的阶段性形态,或者乐观地说:阶段性成果。
如果说内容的差异成就作品的个性,那么,观演关系的变革则可能创造新的戏剧样式。从“黑匣子”里的先锋实验,到山水田园间的实景演出,创作者不断尝试新的演艺空间、演出模式,努力推动戏剧艺术创新发展。在此过程中,《绝对信号》《同船过渡》《如梦之梦》《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作品,都留下了它们的名字。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曹林认为,当今时代,戏剧演出是多向性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戏剧活动竞相出现,戏剧的场域无处不在。所谓剧场艺术之“剧场”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用来承载戏剧表演的物理空间,而是更接近“磁场”的意思,它是艺术行为、艺术作品相互作用的共享空间,与生活中的现实场域相平行。
在国内外理论思考与艺术实践的洗礼下,戏剧的观念、形态发生着变化。以内外双重视角观照沉浸式戏剧,其发展繁荣的理路似乎变得更为清晰。然而,那个观众没有义务回答的问题,专业人士却不得不回答:那些呼唤观众深度参与的戏剧作品,究竟是戏剧还是真人互动游戏?这个问题也许触及某些重大的课题或变革。剧评人安妮认为,《无人入眠》这类作品让人们尽可能地沉浸在戏剧营造的世界,尽管观众可以参与,但无论观众做什么,几乎都不会对戏剧世界造成影响,而对于有些作品来说,观众的个人选择、个人叙事叠加在戏剧世界之上,很可能影响或改变故事的走向。倘若如同部分理论家所说,观看行为定义了当代戏剧的本质属性,那么,当观众之于戏剧的关系从观看变成了参与乃至左右,戏剧还是原来的那个戏剧吗?
拆除剧场外那几磴台阶
所谓戏剧性、文学性,究竟是什么?戏剧与文学究竟能带给观众什么?
如果说阿尔托所倡导的那种观众坐在中央,被场景、持续不断的音响包围,以全身心投入、集体狂欢为特点的残酷戏剧被广泛认为是戏剧,那么沉浸式戏剧自然也属于戏剧范畴,这在逻辑上应当没有太大疑问。不过现实中,观众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往往并非逻辑,而是体验。网络平台上,许多网友将沉浸式戏剧与剧本杀甚至密室逃脱相提并论。杭州小伙王旭斌就是个沉浸式戏剧的爱好者,同时是剧本杀“骨灰级”玩家。“虽然玩剧本杀时人手一份剧本,但不到最后一刻还是很难猜出事件的真相、故事的结局,这种边看、边猜、边体验的感觉,和沉浸式戏剧差不多。”王旭斌说,“我知道,专业人士可能认为它俩不是一回事,但对我来说,除了沉浸式戏剧的票更贵、综合体验更好一点,它俩几乎就是一回事。”
这种混同是一个戏剧地位被挑战的危险信号吗?如果能够接受交叉融合、边界模糊是当今艺术共同趋势的观点,那么对于沉浸式戏剧的“剧本杀化”抑或其他什么“化”,就不必太过激动地口诛笔伐,这一变化也许还会带来一些好处。
正如编剧、策划人史航所说,戏剧是有门槛的,剧场外那几磴台阶使得人们不会一不小心就走进来,至少需要买张票。沉浸式戏剧以及带有戏剧元素的各种文化娱乐形式融合着戏剧性、文学性的内核,以风格类型各异但同样新鲜诱人的姿态,拆除了剧场外的那几磴台阶,于是越来越多人进来了。尽管还是要买张票,但观众、玩家至少能够感知,戏剧、文学距离自己并不遥远。让更广泛的群体有机会走近戏剧、走近文学,这显然不是坏事。
那么,所谓戏剧性、文学性,究竟是什么?戏剧与文学究竟能带给观众什么?学术界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旷日持久,这确乎是值得不断探讨但很难给出精准答案的问题。在第九届乌镇戏剧节的小镇对话“文学与剧场”中,知名作家、编剧刘恒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刘恒认为,仅仅文字上的错彩镂金或游刃有余,价值总是有限的,文学与剧场是精神的会餐。“我自己总结,文学与剧场的真正本质是一种对抗。”刘恒说,文学与时间对抗,容易遗忘的人类靠文学来固定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经典的作品成为创造者生命不朽的象征;文学与愚蠢对抗,人类用文学来促使自己清醒,用文学来增强自己的智力;文学与理性对抗,过分相信自己的理性可能产生偏见、导致灾难,文学保留着人类珍贵的感性;文学与复杂的现实对抗,告诉人们怎样更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符合人性的基本需求。“最根本的是,文学与命运、与不确定性对抗,它在精神上抚慰我们,我们进剧场看剧的时候,寻找的正是这个东西。”刘恒说。
文学与戏剧形而上的价值理想,总要以具体、生动、可实操的方式体现在一部部作品之中。探讨爱、死亡、人性、命运、时代等重大母题的戏剧作品,古今中外都不乏佳作,从《哈姆雷特》到《雷雨》,从《等待戈多》到《茶馆》,不一而足。对于部分沉浸式戏剧以及更具融合性、实验性的文娱形态来说,处理重大命题的创作冲动犹在。戏剧团体“爪马戏剧”打造的《玩家 the life》融合了戏剧表演、桌游、线下社交等元素,定位为“沉浸式互动演绎”。在《玩家 the life》中,每一位观众都被设定为登录虚拟游戏的玩家,玩家使用的游戏币则是时间、智慧、健康、颜值等人生中颇为珍贵的财富。不同的价值、财富应当怎样权衡取舍?的确是伤脑筋的问题,《玩家 the life》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唤起对时间、生命等重大命题的思考。这种思考带有艺术、游戏的特征,无法解决人生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然而思考过与始终懵懂终归不同,增加生命的厚度、深度与丰富性,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意义,也是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需要戏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过山车与莎士比亚本不矛盾
戏剧或言艺术之于观众,是一种单纯技术性、服务性的满足,还是肩负启迪、滋养、引领的使命?打造具有莎士比亚气质的过山车,会不会更吸引人呢?
任何事物尤其是新生事物,都难免在获得追捧的同时遭受质疑,前者证明了该事物存在的价值,后者指出了该事物进化的方向。毁誉参半是常态,喜欢沉浸式戏剧和类似文娱项目的人能够从中感受沉浸带来的美好,而不喜欢它的人则反而感受到紧张、疏离甚至空洞。
的确,并不是所有的沉浸式戏剧或相关文娱项目都有捍卫文学性、戏剧性等价值内核的自觉。在求新求异的冲动、激烈的市场竞争、新技术的蠢蠢欲动以及变现的急迫心情等共同作用之下,不少沉浸项目形式大于内容、体验大于内涵、噱头大于实质。原本,文学性、戏剧性借助新的形式而飞入寻常百姓家,而后者逐渐成熟之后,则可能成为科幻电影中背弃了人类的人工智能,张扬起极度商业化的、消费主义的自我意识,在纯感官的道路上狂奔,文学性、戏剧性已经被抛诸脑后。
当然了,不少传统的、相对严肃的戏剧,也不见得有多么强烈的价值自觉,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经历野蛮生长或者自愿做出选择,都是很自然的现象,不至于为之椎心泣血。只不过,从来没有一部内涵阙如的作品成为经典或者爆款,这是时间和市场宣告的事实。那么,“过山车一定比莎士比亚更吸引人”的看法,是一厢情愿的假设,还是经过了市场检验的真理,抑或是自作聪明的偏见乃至思想缺席的借口?戏剧或言艺术之于观众,是一种单纯技术性、服务性的满足,还是肩负启迪、滋养、引领的使命?打造具有莎士比亚气质的过山车,会不会更吸引人呢?有些东西本就并非势同水火、非此即彼,没理由自矜高傲,也不必太过屈尊降贵。
暂时搁置思想价值问题,仅就形式而言,沉浸式戏剧也受到部分观众的质疑。读中文系的小谢将元杂剧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也经常光顾剧场。小谢表示,他更喜欢传统镜框式舞台的戏剧样式,“第四堵墙”的存在为他构筑起心理屏障,能够给予他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我反而更能沉浸到剧情、人物与戏剧氛围之中。一帮演员围着我演戏的沉浸式戏剧我也看过,常常感到紧张无措,我不知道下一秒他们要干什么,会不会突然把我拉起来演一段儿,这种担心让我惴惴不安,很难投入剧情。”小谢说,“如果沉浸式戏剧开演之前能把剧本发给我,可能会缓解我的紧张,但那样的话,我更分不清自己是看戏的还是演戏的,是该买票还是卖票了。”当然,换个角度观照,看戏的和演戏的也许根本不需要区分,至于票,肯定要买,否则沉浸的费用从哪来?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刘洋认为,目前,沉浸式戏剧的“沉浸”主要体现在空间场所、环境体验层面,而不一定是心理、情感、文化层面。然而,一部作品与观众的真正距离恰恰主要体现在心理、情感和文化上,物理空间的消弭未必带来心理距离的拉近,有时甚至适得其反。这种微妙的审美心理不仅关乎沉浸式戏剧创作的得失,而是有着更具普遍性的意义。
从操作难度上考量,空间场所上的沉浸并不太难,在沉浸中安排吃喝玩乐也不太难,资金到位后,艺术问题主要成了施工问题。然而,敢想、敢做毕竟不等于才华与生命力。艺术作品要真正实现与观众的精神对话,光靠“推墙破框”恐怕不够,光靠新鲜刺激恐怕也不够。那么怎样才够呢?事情发展到这里,似乎就又回到了文学性、戏剧性这个经典命题之上。
以长线的、历史的眼光看,戏剧不断启发、滋养其他艺术形式、文娱方式,这是戏剧生命力旺盛的表现,其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觅得更多的知音、惠及更广的群体。然而,当生活中处处是“戏剧”,可能也同时意味着,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戏剧。因此当务之急或许是:生活中不妨处处是“戏剧”,但戏剧,应该始终在场。
源自:中国文化报
戏剧演出应该是什么样的?台上声台行表、全情投入,台下鸦雀无声、正襟危坐,大概是多数人印象中的情形。而观众“质问”演员、将演员问得“张口结舌、变了脸色”,这种场面大约会令人想到演出事故,但对于一些沉浸式戏剧来说,这正是新鲜的玩法、不同的体验。
从经典之作《无人入眠》到新秀《疯狂理发店》《阿波罗尼亚》等,各类沉浸式戏剧你方唱罢我登场。近年来,沉浸式戏剧在国内演出市场上大量涌现,受到许多观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其发展态势堪用如火如荼来形容。随着不同艺术门类、文娱方式的对话交流,越来越多带有戏剧元素的演艺项目加入沉浸的行列,丰富甚至挑战着传统的戏剧观念和演艺格局,也再次唤起人们对戏剧性、文学性的思考,成为令人瞩目的行业现象和文化景观。
从观看到参与,方兴未艾
尽管沉浸式戏剧有着较为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创作实绩,然而究竟什么是沉浸式戏剧?
沉浸式戏剧以新颖的演出形式、新鲜的观看体验成为市场的新晋宠儿,实际上,沉浸式戏剧并不很年轻,其历史已有数十年之久。资料显示,1975年,设计师尤金·李把一座剧场改建成游艺场,场内不仅有演出,还设有游戏机、小吃摊位、照相馆等,观众可以自由漫步,自行决定观看哪个演出,或者吃些小吃、喝点啤酒——这就是美国演艺项目《冷酷大教堂》,其艺术影响力延续至今。
多年来,为了给观众提供新鲜感、沉浸感,国内创作者想出了许多办法突破原有的演出模式,刷新戏剧的观演方式。以《奋不顾身的爱情》为代表,一些小剧场话剧虽然仍在传统的镜框式舞台上演出,但演员会配合剧情发展而在某些时刻来到观众席中表演,拉近剧情与观众的距离;以赖声川执导的话剧《如梦之梦》为代表的一批作品使用环绕式舞台或者将表演区域延伸到观众席中,沉浸感进一步增强;各大旅游景区的文旅演艺剧经常把舞台设置在真实的山水园林之间,戏剧环境与更广阔复杂的自然、人文环境相融合;被誉为沉浸式戏剧天花板的《无人入眠》在其演出场地设置了几十个房间、同时上演着不同的剧情,观众可以自行选择房间来观看,还有机会与演员互动。这些演出形式各不相同,但都笼统地冠以“沉浸”之名。
尽管沉浸式戏剧有着较为丰厚的历史积淀和创作实绩,然而究竟什么是沉浸式戏剧,从业者、理论界往往莫衷一是。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者阿诺德·阿隆森提出的一个比较简单、通用的定义,基本能够囊括各种看法之间的共识,即“沉浸式戏剧是一个参与性的演出事件,包括一个包罗万象的吸纳性环境,调动了所有的感觉”。以此观之,目前一部分被称为沉浸式戏剧的作品、演艺项目实际上并不十分沉浸,而更像是特殊场域展演,或处于特殊场域展演与沉浸式戏剧的中间地带。
有的在徘徊,有的很激进,不乏创作者步子迈得很大,在作品中尽可能调动多重感官并且大量“留白”,呼唤观众参与。自2017年起从英国引进、经本土化改编后落地上海的《玩味探险家》《玩味放映厅》等“玩味”系列剧集定位为赏味环境剧,将戏剧与饮食结合起来,观众不仅可以观剧、即兴互动,还能同时大快朵颐,不少观众表示很好玩、很好吃。不过,这究竟是戏剧还是真人互动游戏?许多观众在沉浸过后收获了轻松愉悦,未必会考虑这个问题。作为观众,也的确没有回答这一问题的义务。
此剧场已非彼剧场
那些呼唤观众深度参与的戏剧作品,究竟是戏剧还是真人互动游戏?
《玩味探险家》总制作人谢已在采访中表示,沉浸式戏剧“最本质的要求”就是要做一个足够新鲜、吸引人的东西,一种观众在网上无法体验的东西,于是给观众一个走出家门、来到现场的理由。
这种观点是在线上与线下、戏剧与其他相互竞争的语境中看待沉浸式戏剧的。的确,沉浸式戏剧的走红与新兴媒体的影响、文化消费方式的变革升级、激烈的市场竞争等密切相关。在注意力经济的背景下,许多曾经相隔甚远的文娱品种,一下子成了彼此的竞品,相互之间的切磋、借鉴、共融自然而然地发生。正如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韩生所说,交叉融合、边界模糊是当今艺术的共同特点,其背后是整体文化生态的沿革,源自当今社会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的深刻转型。当代观众能够轻松便捷地通过多种媒介形式获取不同的文化娱乐享受,新媒体、新技术也催生了全新的消费场景、消费体验,高速移动互联网、智能穿戴设备等的普及,还将进一步加速这一进程。垂直分众的供给、丰富多元的选择大幅提升了人们在文化消费中的自主性、能动性,观众对戏剧的审美期待、戏剧人的创作方式也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改变。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教师韦哲宇分析,寻求消费市场的戏剧创作者一方面引入各类景观,通过演出场域的技术、装置等为观众呈现银幕、屏幕所难以提供的精致影像和奇观;另一方面,当代戏剧也在创作和演出中鼓励游戏,让观众尽可能获得即兴、自由、创造性等在其他渠道较少享受到的差异化消费体验。不难发现,上述两种诉求在沉浸式戏剧创作演出中交相辉映,戏剧成为“幻觉机器”,让观众暂时进入虚构时空、抽离自身的社会属性,在一场戏的时间里成为某位他者,这既是体验,也是表演。表演的冲动堪称人类自古以来便具有的精神文化需求甚或一种天性,在不同社会、时代条件下被以不同的方式满足,眼下沉浸式戏剧的火爆,正是一种天性解放,恰逢其时。
某事物的蓬勃发展除了外部环境的刺激,也必定有内生动力的推动。沉浸式戏剧是戏剧人对日益挑剔的演出市场做出的积极回应,也是戏剧自身在特定条件下不断求新求变的阶段性形态,或者乐观地说:阶段性成果。
如果说内容的差异成就作品的个性,那么,观演关系的变革则可能创造新的戏剧样式。从“黑匣子”里的先锋实验,到山水田园间的实景演出,创作者不断尝试新的演艺空间、演出模式,努力推动戏剧艺术创新发展。在此过程中,《绝对信号》《同船过渡》《如梦之梦》《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等作品,都留下了它们的名字。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长曹林认为,当今时代,戏剧演出是多向性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戏剧活动竞相出现,戏剧的场域无处不在。所谓剧场艺术之“剧场”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用来承载戏剧表演的物理空间,而是更接近“磁场”的意思,它是艺术行为、艺术作品相互作用的共享空间,与生活中的现实场域相平行。
在国内外理论思考与艺术实践的洗礼下,戏剧的观念、形态发生着变化。以内外双重视角观照沉浸式戏剧,其发展繁荣的理路似乎变得更为清晰。然而,那个观众没有义务回答的问题,专业人士却不得不回答:那些呼唤观众深度参与的戏剧作品,究竟是戏剧还是真人互动游戏?这个问题也许触及某些重大的课题或变革。剧评人安妮认为,《无人入眠》这类作品让人们尽可能地沉浸在戏剧营造的世界,尽管观众可以参与,但无论观众做什么,几乎都不会对戏剧世界造成影响,而对于有些作品来说,观众的个人选择、个人叙事叠加在戏剧世界之上,很可能影响或改变故事的走向。倘若如同部分理论家所说,观看行为定义了当代戏剧的本质属性,那么,当观众之于戏剧的关系从观看变成了参与乃至左右,戏剧还是原来的那个戏剧吗?
拆除剧场外那几磴台阶
所谓戏剧性、文学性,究竟是什么?戏剧与文学究竟能带给观众什么?
如果说阿尔托所倡导的那种观众坐在中央,被场景、持续不断的音响包围,以全身心投入、集体狂欢为特点的残酷戏剧被广泛认为是戏剧,那么沉浸式戏剧自然也属于戏剧范畴,这在逻辑上应当没有太大疑问。不过现实中,观众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往往并非逻辑,而是体验。网络平台上,许多网友将沉浸式戏剧与剧本杀甚至密室逃脱相提并论。杭州小伙王旭斌就是个沉浸式戏剧的爱好者,同时是剧本杀“骨灰级”玩家。“虽然玩剧本杀时人手一份剧本,但不到最后一刻还是很难猜出事件的真相、故事的结局,这种边看、边猜、边体验的感觉,和沉浸式戏剧差不多。”王旭斌说,“我知道,专业人士可能认为它俩不是一回事,但对我来说,除了沉浸式戏剧的票更贵、综合体验更好一点,它俩几乎就是一回事。”
这种混同是一个戏剧地位被挑战的危险信号吗?如果能够接受交叉融合、边界模糊是当今艺术共同趋势的观点,那么对于沉浸式戏剧的“剧本杀化”抑或其他什么“化”,就不必太过激动地口诛笔伐,这一变化也许还会带来一些好处。
正如编剧、策划人史航所说,戏剧是有门槛的,剧场外那几磴台阶使得人们不会一不小心就走进来,至少需要买张票。沉浸式戏剧以及带有戏剧元素的各种文化娱乐形式融合着戏剧性、文学性的内核,以风格类型各异但同样新鲜诱人的姿态,拆除了剧场外的那几磴台阶,于是越来越多人进来了。尽管还是要买张票,但观众、玩家至少能够感知,戏剧、文学距离自己并不遥远。让更广泛的群体有机会走近戏剧、走近文学,这显然不是坏事。
那么,所谓戏剧性、文学性,究竟是什么?戏剧与文学究竟能带给观众什么?学术界关于文学性的讨论旷日持久,这确乎是值得不断探讨但很难给出精准答案的问题。在第九届乌镇戏剧节的小镇对话“文学与剧场”中,知名作家、编剧刘恒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刘恒认为,仅仅文字上的错彩镂金或游刃有余,价值总是有限的,文学与剧场是精神的会餐。“我自己总结,文学与剧场的真正本质是一种对抗。”刘恒说,文学与时间对抗,容易遗忘的人类靠文学来固定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经典的作品成为创造者生命不朽的象征;文学与愚蠢对抗,人类用文学来促使自己清醒,用文学来增强自己的智力;文学与理性对抗,过分相信自己的理性可能产生偏见、导致灾难,文学保留着人类珍贵的感性;文学与复杂的现实对抗,告诉人们怎样更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符合人性的基本需求。“最根本的是,文学与命运、与不确定性对抗,它在精神上抚慰我们,我们进剧场看剧的时候,寻找的正是这个东西。”刘恒说。
文学与戏剧形而上的价值理想,总要以具体、生动、可实操的方式体现在一部部作品之中。探讨爱、死亡、人性、命运、时代等重大母题的戏剧作品,古今中外都不乏佳作,从《哈姆雷特》到《雷雨》,从《等待戈多》到《茶馆》,不一而足。对于部分沉浸式戏剧以及更具融合性、实验性的文娱形态来说,处理重大命题的创作冲动犹在。戏剧团体“爪马戏剧”打造的《玩家 the life》融合了戏剧表演、桌游、线下社交等元素,定位为“沉浸式互动演绎”。在《玩家 the life》中,每一位观众都被设定为登录虚拟游戏的玩家,玩家使用的游戏币则是时间、智慧、健康、颜值等人生中颇为珍贵的财富。不同的价值、财富应当怎样权衡取舍?的确是伤脑筋的问题,《玩家 the life》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唤起对时间、生命等重大命题的思考。这种思考带有艺术、游戏的特征,无法解决人生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然而思考过与始终懵懂终归不同,增加生命的厚度、深度与丰富性,本身就是一种非凡的意义,也是人类之所以需要文学、需要戏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过山车与莎士比亚本不矛盾
戏剧或言艺术之于观众,是一种单纯技术性、服务性的满足,还是肩负启迪、滋养、引领的使命?打造具有莎士比亚气质的过山车,会不会更吸引人呢?
任何事物尤其是新生事物,都难免在获得追捧的同时遭受质疑,前者证明了该事物存在的价值,后者指出了该事物进化的方向。毁誉参半是常态,喜欢沉浸式戏剧和类似文娱项目的人能够从中感受沉浸带来的美好,而不喜欢它的人则反而感受到紧张、疏离甚至空洞。
的确,并不是所有的沉浸式戏剧或相关文娱项目都有捍卫文学性、戏剧性等价值内核的自觉。在求新求异的冲动、激烈的市场竞争、新技术的蠢蠢欲动以及变现的急迫心情等共同作用之下,不少沉浸项目形式大于内容、体验大于内涵、噱头大于实质。原本,文学性、戏剧性借助新的形式而飞入寻常百姓家,而后者逐渐成熟之后,则可能成为科幻电影中背弃了人类的人工智能,张扬起极度商业化的、消费主义的自我意识,在纯感官的道路上狂奔,文学性、戏剧性已经被抛诸脑后。
当然了,不少传统的、相对严肃的戏剧,也不见得有多么强烈的价值自觉,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经历野蛮生长或者自愿做出选择,都是很自然的现象,不至于为之椎心泣血。只不过,从来没有一部内涵阙如的作品成为经典或者爆款,这是时间和市场宣告的事实。那么,“过山车一定比莎士比亚更吸引人”的看法,是一厢情愿的假设,还是经过了市场检验的真理,抑或是自作聪明的偏见乃至思想缺席的借口?戏剧或言艺术之于观众,是一种单纯技术性、服务性的满足,还是肩负启迪、滋养、引领的使命?打造具有莎士比亚气质的过山车,会不会更吸引人呢?有些东西本就并非势同水火、非此即彼,没理由自矜高傲,也不必太过屈尊降贵。
暂时搁置思想价值问题,仅就形式而言,沉浸式戏剧也受到部分观众的质疑。读中文系的小谢将元杂剧作为研究对象,同时也经常光顾剧场。小谢表示,他更喜欢传统镜框式舞台的戏剧样式,“第四堵墙”的存在为他构筑起心理屏障,能够给予他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我反而更能沉浸到剧情、人物与戏剧氛围之中。一帮演员围着我演戏的沉浸式戏剧我也看过,常常感到紧张无措,我不知道下一秒他们要干什么,会不会突然把我拉起来演一段儿,这种担心让我惴惴不安,很难投入剧情。”小谢说,“如果沉浸式戏剧开演之前能把剧本发给我,可能会缓解我的紧张,但那样的话,我更分不清自己是看戏的还是演戏的,是该买票还是卖票了。”当然,换个角度观照,看戏的和演戏的也许根本不需要区分,至于票,肯定要买,否则沉浸的费用从哪来?
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刘洋认为,目前,沉浸式戏剧的“沉浸”主要体现在空间场所、环境体验层面,而不一定是心理、情感、文化层面。然而,一部作品与观众的真正距离恰恰主要体现在心理、情感和文化上,物理空间的消弭未必带来心理距离的拉近,有时甚至适得其反。这种微妙的审美心理不仅关乎沉浸式戏剧创作的得失,而是有着更具普遍性的意义。
从操作难度上考量,空间场所上的沉浸并不太难,在沉浸中安排吃喝玩乐也不太难,资金到位后,艺术问题主要成了施工问题。然而,敢想、敢做毕竟不等于才华与生命力。艺术作品要真正实现与观众的精神对话,光靠“推墙破框”恐怕不够,光靠新鲜刺激恐怕也不够。那么怎样才够呢?事情发展到这里,似乎就又回到了文学性、戏剧性这个经典命题之上。
以长线的、历史的眼光看,戏剧不断启发、滋养其他艺术形式、文娱方式,这是戏剧生命力旺盛的表现,其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觅得更多的知音、惠及更广的群体。然而,当生活中处处是“戏剧”,可能也同时意味着,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戏剧。因此当务之急或许是:生活中不妨处处是“戏剧”,但戏剧,应该始终在场。
源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