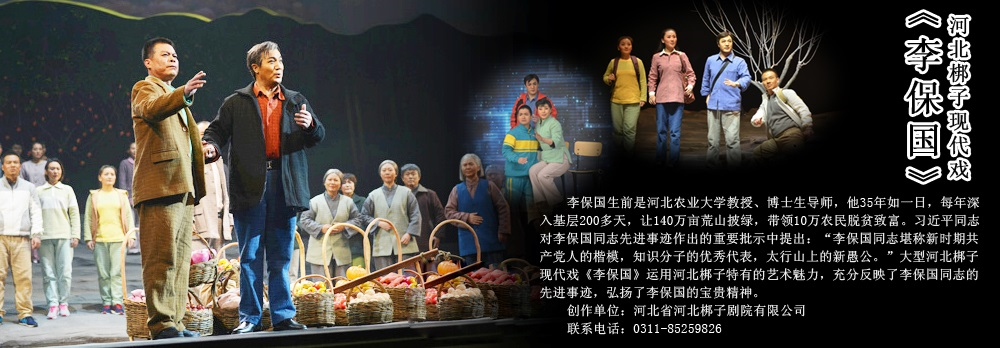——基于文化视角的中国当代舞蹈创作理念阐释兼论当代安徽舞蹈艺术发展
戴 虎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并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文从当代中国舞蹈创作的视角,从“地域”“民族”“专业(学科)”三个维度,从何谓“守正”与“守旧”、“尊古”与“复古”两个向度,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典舞蹈艺术作品,聚焦近些年涌现的具有代表性的舞蹈艺术作品,通过选材主题、形式设计、语言特质、编导理念等具体分析路径,为深入阐释中华文明历史特性提供一个“舞蹈”的视角。同时,本文立足中华舞蹈文明多元共生的视角,在共时的层面,对当代安徽舞蹈艺术的创作与发展进行了纵向梳理,提出从“大舞蹈”“大格局”“体系化”的人文视角出发,或可助力新时代安徽舞蹈艺术发展再攀新高。

安徽艺术学院舞蹈学院2023年创作剧目《纸韵千年》 黄凯迪 摄

安徽艺术学院舞蹈学院2023年创作剧目《花上春》 黄凯迪 摄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并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建设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他在讲话中还提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做到“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这与“双创理论”“四个自信”可谓一脉相承。
对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特别是舞蹈事业发展的工作者而言,要对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舞蹈文化中的“正”与“旧”、“尊”与“复”有一个相对清晰和明确的厘清或笃定,首先需要从文化观念认知层面上,系统性、纲领性地廓清“正”与“旧”的边界,从而渐进地实现温故知新。
一、动态把握文化历史延续与时代演替之间的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时间隧道里,面对浩瀚的中华文化,试图以“正”与“旧”概念界定廓清其边界,作为单一的个体显然是不可能的。
艺术作为精神文化的载体,存在着内在精神和形式上的连续性与演替性,存在着沿袭和革新的内在张力。有沿袭而不讲革新,它会窒息自己的生机,但只讲革新而不考虑内在精神和形式上的连续性,也可能使它失去了存在的依托,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前些年国外评论界有一种论调,认为那些表现中国所谓传统社会或变革时期的作品更具“中国味道”,才是好作品。乍一听的确应该沾沾自喜,但其实这其中隐藏着某种微妙的歧视。在面对与自己平等的文艺作品时,他们寻找的是艺术价值,会用与其评读本国文艺作品时一样严苛的艺术标准来褒贬对方,而且毫不留情。为什么在转向中国文艺作品时,“中国味道”却成为一个评价的标准?究其原因,一个因素是当代中国社会、中国文艺仍旧被一些西方人当作社会学辅助材料,他们依然带有一种居高临下俯视观察的偏见,他们希望看到的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中国味道”,一旦不是,就会感到失望。这种误读、偏读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和源于何种视角,都不应该是我们主要关注的。
当务之急在于,我们中有不少人沉浸在这种“虚幻的褒奖”中而不自知。当这种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味道”成为一种奋斗目标和价值标准,就出现了华夏大地争相追逐、复制、放大这种“中国风”的现象。这其中存在“欧洲中心论”的变异、“文化进化论”的影响,也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现代选择缺乏自知、自觉、自信的一种表现。
近几年,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造出两部中国舞蹈界的现象级作品,一部是由新生代导演韩真、周莉亚担任总导演的《只此青绿》,一部是由国际著名舞蹈家、编导、画家、视觉设计师沈伟担任总导演的舞蹈诗剧《诗忆东坡》。从名字即可看出,这两部作品都是以中国传统艺术、人文精神为叙事主题的舞剧。出品方表示:“从‘青绿’至‘东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次致敬,培育中国文化表达走向世界艺术体系,是一场深入阐发古今美学与精神哲思的艺术实践,是一次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时代性、国际性艺术创新探索。”这两部作品,也正是以世界性的语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个案。
在安徽省,近些年也有类似“制作精良、艺术精湛、思想精深”的好作品,比如2011年的舞剧《徽班》(安徽省歌舞剧院创演)、2020年的舞剧《石榴花开》(安徽省花鼓灯歌舞剧院创演)等,再往更远时期,还有老一辈舞蹈艺术家娄楼、赵新盟夫妇的《兰花赋》《算盘声声》,等等。特别需要介绍的是安徽为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的一部歌舞剧——《玩灯人的婚礼》,这部作品在当时得到专家和观众的高度赞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部作品没能广泛传播开来。
二、辩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与世界交互的自洽
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或者说是面对世界文化信息交流下传统文化的现代选择,在既往的研究范式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良态势。
一种是“削足适履”式。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简单粗暴,采取非黑即白、非优即劣、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模式,抹杀了中国民间许多具有“在之间”的灰色的、模糊性的文化基因,更为遗憾的是,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营造出先进与落后、愚昧与文明、封建与现代的绝对价值标准,严重打击了民间从业者的自信,致使这些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失去了活力。
这种削足适履式的做法还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交流的态度上。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降,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到“全盘西化”的胡适之,到主张“融通中西”的王国维、陈寅恪,再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季羡林,中学与西学之争始终存在于几代中国学者之间。对待不同时代的贤者,我们无须进行谁对谁错的评判,需要做的是从历史事实中汲取实践经验和智慧成果。
从西方引入的现代教育制度,应该是我们学之“器”,而非学之“本”,更非学之“道”。我们不应该把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文明果实,笼统地都装进从西方引入的理论、概念这些篮子中。更错误的是,一些人把装不进去的或者装进去不舒服的,就直接漠视、丢掉甚至贴上“落后”“不文明”的标签彻底抛弃,这与那些个削足适履、努力挤进灰姑娘水晶鞋的“拜金女”何异?殊不知,即使鲜血淋漓地穿上水晶鞋,你仍然不会是王子心目中的公主。
另一种是“囫囵吞枣”式。客观地说,传统文化中的确有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习俗、规则、审美范式,比如“三寸金莲”“活体祭祀”“等级门户”“轮亲换亲”“多妻多夫”等,这些与现代文明相背离的野蛮之举,的确应该被时代所抛弃,甚至以法律形式禁止。对这些价值评判泾渭分明的“传统”进行甄别取舍,已经不是现代文化选择的难点。困惑处在于上文提到的“在之间”的价值性模糊的文化行为,也即“正”与“旧”、“尊”与“复”之间的边界幅度。对此,不能简单粗暴地摒弃,也不能囫囵吞枣地吸收。有些事物、行为的价值现在搞不清,不代表将来搞不清,今天不懂的,不代表明天也是糊涂的。所以,暂时不清楚、不明白、拿不准的,或许可以允许其自然存续和发展,下一站也许就明白了该继续行走还是下车,所需要的是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的选择时,多一些细致、周详的考察和足够的耐心、包容。
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囫囵吞枣式借鉴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后的文化心理和生理的排异反应,从而不再认识自己是谁、从何而来,更严重者,这种文化态度可能会阉割自身文化延续的根脉,导致传统文化的断流,这就是常说的“文化安全失范”。
笔者并不否认,20世纪前期,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教育观念、审美理论,借另一种眼光打量自己、重新审视自己,因此出现了新视野、新境界,推进了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比如新中国早期在中国古典舞建立与现代舞剧、舞蹈创作中对芭蕾、苏联舞蹈创作范式的借鉴,的确助力开创了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中国舞蹈事业的一个高潮。比如《荷花舞》《红绸舞》《鄂尔多斯》《飞天》《丰收歌》等舞蹈作品,《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宝莲灯》《小刀会》等舞剧,及至新时期的《丝路花雨》《二泉映月》《黄土地》《大红灯笼高高挂》《大梦敦煌》等,都在创作理念与编舞方式上受到西方舞台艺术创作的影响。
应该清醒地看到,西方眼光和思维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本体上是有所错位的,我们借鉴和引入的是西方经验的理论定位,而他们在创造理论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存在。这种他者眼光是有启发作用的,这种启发作用不仅在于那些术语和概念,而且在于从经验到形成理论的方法和过程。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过程的价值往往大于孤立地借鉴术语和理论的价值。
我们不能做夜郎自大的井底之蛙,更不学那个涨爆肚皮只为和牛一较大小的蛤蟆。今天的信息社会,文化的交互作用无处不在,无谓的争论没有价值。未来人类的文明秩序,目前广受认可的观点一是继承传统,二是保持创造力。而在继承传统与保持创造之中,拥有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必有态度。需要清醒认识的是,任何学习、借鉴、转用、引入都应该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之内,都应该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内部,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深刻理解‘两个结合’重大意义”的现实印证。
三、整体把握中华现代文明建设中的地域性、超越性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自古以来,多民族、多地域、多族群、多人种、多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致使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因此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有意思的是,与这种“超越性”相对应的中华文化“地域性”“民族性”“专业化”,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为舞蹈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语言素材与诗意想象。比如20世纪60年代蜚声中外的《摘葡萄》《洗衣歌》《牧羊女》《鄂尔多斯》等、21世纪初叶的《丰收时节》《淮河畔的玩灯人》《酥油飘香》等,乃至于近些年安徽的《说兰花》(编导:黄奕华)、《徽娘》(编导:张晓梅、袁莉)、《一条大河》(编导:欧阳吉芮)、《兰花》(编导:许姝、王达)、《看花灯》(编导:苏纳)、《淮畔春语》(编导:王珊珊)、《淮水情兰花弯》(编导:高度、黄奕华,表演:北京舞蹈学院)、《淮河边的玩灯人》(编导:赵铁春、武帅、金明)、《淮河共乡土》(编导:于晓雪、徐祭红)、《渡江》 (编导:王成),以及合肥演艺集团、合肥市歌舞团创演的《延乔兄弟》《大湾春歌》,安徽省花鼓灯歌舞剧院等创演的《沁园春·灯窝》等,单从字面上,就能看出延续近40年的安徽舞蹈舞台艺术创作的地域性。
然而,地域性强烈的风格与标识,又像是一个禁锢,把舞蹈本具有的隐喻、象征、批判、阐释的可能性圈定在自然空间的边界,如此令安徽舞蹈艺术更多地成为一种地方性的风情、风景,更甚者,成为一种形象的图解、翻译、导游。
进入新时代,对舞蹈创作地域性,特别是民间舞蹈创作风格性的讨论总是存在着威严的话语,在其看来,似乎所有的地域性问题,要么有待拯救改造,要么亟须继承发扬。有意思的是,这样的认识有时会衍生出一种基于自然空间的等级判断。比如,当地域性遭遇“北京”“海派”乃至“沿海”这样的地理名词,彰显的大约是“优质”;而当地域性与某些区域性拥抱,则难免会有“渐次”的羞愧,甚至因为经济、科技、教育的落差,对舞蹈地域性的言说更像是先富起来的优势群体以观光客、猎奇的目光对“地方风情”和“异质经验”的垂爱。诗人沈苇曾说:“文学的‘中心——边缘论’,已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学话语,而是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和社会话语的偷换、借用。”以此观舞蹈创作者的地域性身份,也是如此。
“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由此,对舞蹈地域性的身份,存在边界横向拆除与深度开掘两个维度的延宕。一方面,创作者们以集群或成系列的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舞蹈作品,借助地域性的特质表达而直指普遍的人心、抵达普遍的人性;另一方面,以精练选材、精妙构思、精致技法,依托安徽地区乃至江淮地区自然景观的幽独与人文景观的独然,淬炼舞蹈作品的内在精神肌理,从风俗、风景走向风雅、风致。
说到底,舞蹈创作的根本还是怎么看世界、怎么表达世界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以“民族”识别的舞蹈作品自有其场域下的“魅与惑”。一方面,民族特有的风俗为舞蹈创作提供了现实与想象沟通的开阔地;另一方面,舞蹈对世界的表达不得不有所规矩——想象之门虚掩而精神窄门忽现。民族风俗与舞蹈创作的关系尽管耐人寻味,其底色仍是不受“民族身份”限制的普适性情怀,如戴爱莲的《飞天》、康巴尔汗的《盘子舞》、贾作光的《牧马舞》、张继钢的《黄土黄》、王玫的《独树》、李楠的《弦歌悠悠》……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所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其此之谓,优秀舞蹈艺术家总是凭借建构专属的舞蹈地理空间,获得思想表达的自由。
一名艺术家如果创造出的作品仅仅为“我们(内部)”喜欢、认可,是具有一定意义也是需要的,但更进一步,一个作品不仅要“我们”喜欢,还要“你们”也喜欢、“他们”也喜欢,最为理想的当然是“大家”都喜欢。
舞蹈作品《中国妈妈》之所以感动了无数观众,正是源于人们对于母爱这一人类共通情感的深度共鸣。创作者没有把目光聚焦于这位伟大母亲的“民族”身份,也未刻意渲染收养孩子们的“地域”背景,更没有将作品选材局限于什么“风格”属性,而是以生活化的情节、平民化的视角对人类共通的母爱进行了生动而深情的表达。正是这种共通的、超越的母爱通约性,强化了作品对不同民族情感和心灵的润泽和凝聚作用,从而形成以作品为内核的情感共鸣“共同体”。
小人物可以有大情怀、大格局,小故事也可以有大主题、大内涵,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发现,又如何去讲述。歌舞艺术创作呈现的共通,就是要从民族性的风景、风俗中挖掘具有时代风尚的“有意味”形式;从地方性的情绪、情景中开掘具有普适情怀的“这一个”历史事件(人物),从而创作出能“鼓民力、开民智、体民苦、聚民心”的歌舞艺术作品。
舞蹈是人类文化和情感表达的一种方式。作为安徽地域文化结构中的一大亮点,“花鼓灯”在当下作为一张风光名片迎合着外界的目光。从舞蹈大师吴晓邦所说“系着土风的升华”,到冯(国佩)、郑(九如)、陈(敬之)花鼓灯流派的出现,再到新时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专业教学的基础课程,安徽因为“花鼓灯”而被人们念念不忘。不过,这样的想象往往带有好奇甚至标签化的意念,而一个被审美、被消费、被向往的安徽和安徽文化,主体性也可能会被限定。那么,从舞蹈呈现与表达的可能性来说,所谓的“延拓专业格局”,就需要我们在广度、力度、深度上下功夫,把情绪性的舞蹈与有情怀的文字联通;把风情性的舞蹈图示与有风度的诗意接通;把情景性展现的舞蹈与思想贤哲的想象融通。延拓专业也是在打破区隔意识、打破专业壁垒、打破“血统”纯正的精英化主义,是越过舞蹈风景、风情的遮蔽,去触摸安徽内在的文化脉络,感受现实安徽的社会风尚。
人类不只在人类的源头拥有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在人类的每一时刻,经历自己的经验,说出自己的知识,几乎是人类史得以运行下去的根本因果。
作为现代学科分野的舞蹈专业性是舞蹈文化事业发展的立足点,但不应成为舞蹈创作者的囚笼。从专业性视角的创作,恰恰是从创作者最直接、最灵性也最纠缠的心灵谱系出发的,但在好的创作者那里,我们常看到他们所谓的专业性是虚晃一枪,他们恰恰是以专业性揭示了自我心灵谱系中最为普遍的精神地理。
最近为观众和媒体热议的舞剧《咏春》(编导:韩真、周莉亚,创演:深圳歌剧舞剧院),从武术与舞蹈的内在逻辑与形式语言中生发出令人惊艳的艺术张力。杂技舞剧《东方天鹅》则以舞蹈与杂技的彼此融合,创造了千场演出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此外,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对于电影蒙太奇手法的借鉴,文旅融合剧目“又见”和“只有”系列对于多舞台艺术形式的杂糅、拼接与体系化融合,也已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艺术现象被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这些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艺术介质下的成功个案,其创作的图谱中都共同拥有多门类、多专业、多形式的“跨界”“融合”特点。
诗人沈苇曾提出:“综合抒情、混血之诗的诗学概念,其目的是弥合分裂,实现更高意义上的综合。”今天,作为安徽舞蹈艺术编导,更应该从这样的“预言”中读懂未来,能越过专业的围栏而在更宽广的世界实现更高价值的抒情。舞蹈艺术家、教育家王玫常说:“我喜欢的人与事,事与物,通常不是我们舞蹈圈的,我喜欢哲学,喜欢戏剧,也喜欢历史文学什么的,但我唯有通过舞蹈来表达我自己,舞蹈是我与这个世界沟通的最直接的方式。”有意思的是,喜欢王玫作品的也不仅仅是舞蹈圈的,甚至在王玫看来,读懂她作品的也往往是那些专业之外的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所的孟潇在观看2015年王玫带领其学生创作表演的名为“传统舞蹈的现代性编创”的晚会之后,曾写下这样的文字:“‘伟大的戏剧在继续,而你也可以贡献一首诗。’我想,王玫和她的舞者学生给我的启示是——生活在继续,那么,你的诗是什么?”
结语
我们应该在世界文明版图中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当没有适合自己的道路时,我们应该去研究修路、修桥的工艺,去发现文明创造过程中的智慧,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中国式舞蹈艺术创作之路。这不是文化盲目、敝帚自珍,更非夜郎自大、盲人摸象,而是以历史的思维、时代的眼光、内在的自觉清醒地回到自己的历史深处,廓清“正”与“旧”,厘清“尊”与“复”,温故知新,明白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要去向何方。这是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十六字箴言的真意所在,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殷殷叮咛的深意所在。
(作者系安徽艺术学院舞蹈学院院长、教授)
源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