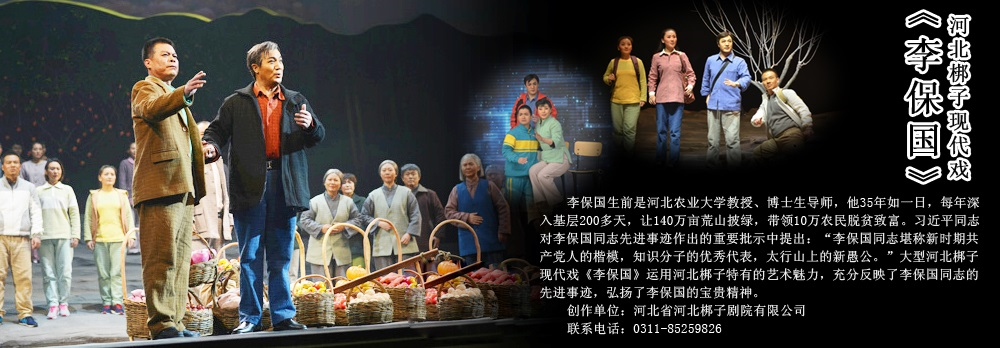戏曲应该发展创新
责任编辑:王琳 发布日期:2014-08-26
毛小雨
毋庸讳言,自从2001年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深入人心,对国内的民间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非遗保护也进入了一些误区:自从有了非遗名分之后,有不少戏曲剧种似乎套上了金钟罩、铁布衫,变得刀枪不入,以遗产“高大上”的名义,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改,如要创新,成了一种背叛或大逆不道的行为。
其实,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提出这个概念到具体实施,基本上也是在摸索前行的。先是在申报过程中讲学术,一个申报文本要写几万字,可能最后发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的专家看起来吃力,于是乎改成了填表,遗产概况逐项填写即可。在名额方面,刚开始一个成员国每两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到后来又改成一个成员国可以申报多个项目。名录也改成了两个,代表作名录和亟须保护的名录。申报文本、申报视频各国也是理解各不相同,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由此可见,该组织的申报指南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它不能涵盖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我国在非遗保护中总结的生产性保护以及活态保护,其实也是不希望把包括戏曲在内的项目固化起来成为一种博物馆艺术。
因此,掌握好非遗保护的度,不要捆绑住戏曲剧种的手脚,使之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是戏曲生存的迫切要求。然而,事与愿违,虽然说大多数戏曲遗产名符其实,是艺术家的杰出创造,代表了一个区域、一个族群民间艺术的最高水平,但也有的剧种,既无剧目的积累,也无高水平的演技。而有些剧种,躺在非遗保护的大树下,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如果别人动一下,就是对遗产的不尊重。这真是天大的误解,也是对戏曲艺术的规律和戏曲剧种一知半解。
有一个我常举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昆曲对《十五贯》的整理改编的成功经验,到现在仍然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十五贯》的剧本改编和导演陈静对剧本编演曾经做过经验总结,因为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不少传统昆曲的拥趸以此为例批评《十五贯》的改编破坏了昆曲的雅致。陈静在改编中认识到昆曲中字少腔多的特点,可能会引起字句分散、词意不明和表演动作上拖沓繁复的问题。改过唱词之后,谨慎的陈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了作曲李荣圻。陈静描述:“李老先生看了后,半晌不言语,只是用手在大腿上拍个不停。我以为是他不同意了,准备向他表示:‘我是外行,是随便改改做实验的。要是不能用,我就照原词格填词好了。您不要为难。’话还没有说出口,李老先生突然说:‘这个样子改,好懂,也好唱,你大胆改吧,你怎么改,我怎么给你谱。’‘不会失掉昆曲的韵味吧?’我问。‘不会不会,板眼都是对头的。’这样一来,我感到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压在心里的大石头似乎轻了许多。于是我就根据构思的提纲先把整个剧本的唱词部分全部写出来了。”
这段生动的对话可以说是给一些貌似懂行的人士一个有力的回击。昆曲并非高不可攀、凛然不可侵犯的东西。作为中国戏曲的一种,它本身也需要发展变化。《十五贯》改编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还有一点也说明,昆曲还是有自我修正的能力的,不是固化以后,就不能改变了。张庚在当时就肯定了这一点,他指出:“这次整理本还有通俗和简洁的大优点。许多用典故堆砌起来的难懂的文言唱词都另写成浅显平易的语言了;许多文言的台词,也改成普通口语或苏州方言了;大段的唱减少了;无论在舞台上或在本子上,看起来都感觉非常简练易懂,又很富于表现力。”
因此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简单地说要使其原汁原味,不是肤浅地把几出折子戏翻来覆去演出就完事大吉,要认识遗产的精髓以及遗产的丰厚博大并加以利用,这才是包括昆曲在内的戏曲剧种的出路。同时,加大创新的力度,戏曲发展才会有更好的出路。
回顾世界戏剧史和中国戏曲史,每次重大发展都和形式的创新有密切关系。当代英美音乐剧之所以成功,就是敢于打破传统歌剧僵化的表演方式,将歌舞有机地融为一体。如安德鲁.L.韦伯的音乐剧《艾薇塔》、《猫》和《歌剧魅影》就是传统歌剧与流行曲风结合得臻于化境的大师作品,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功。
而我们还是希望在原来的基础上敲敲打打、修修补补,仍然没有另起炉灶,建立一套新的戏曲品种的决心。传统戏曲是农耕时代的产物,方言的使用决定了戏曲剧种的地域文化色彩特别浓重。而在信息化时代,就要呼唤一种能适应大多数观众的戏曲形式来。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的音乐定位就是面对全球的观众。正是因为如此,制作人在题材选择上会慎之又慎,虽然没有宣传部门引导,其主题也大多是积极向上、歌颂真善美的。同时,音乐剧作者还会选择经典小说或电影改编,同时还会刻意淡化剧目的地域色彩,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来叙述故事,如《歌剧魅影》。并且有些故事老少咸宜,非常适合家庭为单位的观众欣赏,如《狮子王》、《蜘蛛侠》等。所有这些努力,其实就是为了观众面的最大化,让尽可能多的观众走到剧场中去。
既然戏曲界对王国维称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提法有着基本的认同,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拘泥于戏曲是个什么样子呢?
创造新的戏曲样式或品种已经是戏曲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近20年,当我们看到,小品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品种占据了电视台综艺节目的重要位置,每年的春节晚会如果没有重磅小品就会使导演抓耳挠腮、坐卧不宁时,我们会感同身受,时代变了,观众审美趣味变了,如果戏曲再不变,遭到观众的抛弃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创立已有百年的日本宝冢团之所以历经一个世纪风采依旧,这和创始人小林一三定下的“以歌舞伎为基础,引进西洋歌剧和舞蹈,创立全新的国民戏剧”理念不无关系。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都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但创新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能不能创立全新的中国戏曲呢,这是从业者应该认真思考的事!
源自:中国文化报
毋庸讳言,自从2001年昆曲被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深入人心,对国内的民间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是,非遗保护也进入了一些误区:自从有了非遗名分之后,有不少戏曲剧种似乎套上了金钟罩、铁布衫,变得刀枪不入,以遗产“高大上”的名义,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改,如要创新,成了一种背叛或大逆不道的行为。
其实,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提出这个概念到具体实施,基本上也是在摸索前行的。先是在申报过程中讲学术,一个申报文本要写几万字,可能最后发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的专家看起来吃力,于是乎改成了填表,遗产概况逐项填写即可。在名额方面,刚开始一个成员国每两年只能申报一个项目,到后来又改成一个成员国可以申报多个项目。名录也改成了两个,代表作名录和亟须保护的名录。申报文本、申报视频各国也是理解各不相同,质量也是良莠不齐。由此可见,该组织的申报指南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它不能涵盖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我国在非遗保护中总结的生产性保护以及活态保护,其实也是不希望把包括戏曲在内的项目固化起来成为一种博物馆艺术。
因此,掌握好非遗保护的度,不要捆绑住戏曲剧种的手脚,使之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是戏曲生存的迫切要求。然而,事与愿违,虽然说大多数戏曲遗产名符其实,是艺术家的杰出创造,代表了一个区域、一个族群民间艺术的最高水平,但也有的剧种,既无剧目的积累,也无高水平的演技。而有些剧种,躺在非遗保护的大树下,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如果别人动一下,就是对遗产的不尊重。这真是天大的误解,也是对戏曲艺术的规律和戏曲剧种一知半解。
有一个我常举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昆曲对《十五贯》的整理改编的成功经验,到现在仍然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十五贯》的剧本改编和导演陈静对剧本编演曾经做过经验总结,因为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不少传统昆曲的拥趸以此为例批评《十五贯》的改编破坏了昆曲的雅致。陈静在改编中认识到昆曲中字少腔多的特点,可能会引起字句分散、词意不明和表演动作上拖沓繁复的问题。改过唱词之后,谨慎的陈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了作曲李荣圻。陈静描述:“李老先生看了后,半晌不言语,只是用手在大腿上拍个不停。我以为是他不同意了,准备向他表示:‘我是外行,是随便改改做实验的。要是不能用,我就照原词格填词好了。您不要为难。’话还没有说出口,李老先生突然说:‘这个样子改,好懂,也好唱,你大胆改吧,你怎么改,我怎么给你谱。’‘不会失掉昆曲的韵味吧?’我问。‘不会不会,板眼都是对头的。’这样一来,我感到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压在心里的大石头似乎轻了许多。于是我就根据构思的提纲先把整个剧本的唱词部分全部写出来了。”
这段生动的对话可以说是给一些貌似懂行的人士一个有力的回击。昆曲并非高不可攀、凛然不可侵犯的东西。作为中国戏曲的一种,它本身也需要发展变化。《十五贯》改编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还有一点也说明,昆曲还是有自我修正的能力的,不是固化以后,就不能改变了。张庚在当时就肯定了这一点,他指出:“这次整理本还有通俗和简洁的大优点。许多用典故堆砌起来的难懂的文言唱词都另写成浅显平易的语言了;许多文言的台词,也改成普通口语或苏州方言了;大段的唱减少了;无论在舞台上或在本子上,看起来都感觉非常简练易懂,又很富于表现力。”
因此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简单地说要使其原汁原味,不是肤浅地把几出折子戏翻来覆去演出就完事大吉,要认识遗产的精髓以及遗产的丰厚博大并加以利用,这才是包括昆曲在内的戏曲剧种的出路。同时,加大创新的力度,戏曲发展才会有更好的出路。
回顾世界戏剧史和中国戏曲史,每次重大发展都和形式的创新有密切关系。当代英美音乐剧之所以成功,就是敢于打破传统歌剧僵化的表演方式,将歌舞有机地融为一体。如安德鲁.L.韦伯的音乐剧《艾薇塔》、《猫》和《歌剧魅影》就是传统歌剧与流行曲风结合得臻于化境的大师作品,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功。
而我们还是希望在原来的基础上敲敲打打、修修补补,仍然没有另起炉灶,建立一套新的戏曲品种的决心。传统戏曲是农耕时代的产物,方言的使用决定了戏曲剧种的地域文化色彩特别浓重。而在信息化时代,就要呼唤一种能适应大多数观众的戏曲形式来。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的音乐定位就是面对全球的观众。正是因为如此,制作人在题材选择上会慎之又慎,虽然没有宣传部门引导,其主题也大多是积极向上、歌颂真善美的。同时,音乐剧作者还会选择经典小说或电影改编,同时还会刻意淡化剧目的地域色彩,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来叙述故事,如《歌剧魅影》。并且有些故事老少咸宜,非常适合家庭为单位的观众欣赏,如《狮子王》、《蜘蛛侠》等。所有这些努力,其实就是为了观众面的最大化,让尽可能多的观众走到剧场中去。
既然戏曲界对王国维称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的提法有着基本的认同,那么我们为什么又要拘泥于戏曲是个什么样子呢?
创造新的戏曲样式或品种已经是戏曲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近20年,当我们看到,小品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品种占据了电视台综艺节目的重要位置,每年的春节晚会如果没有重磅小品就会使导演抓耳挠腮、坐卧不宁时,我们会感同身受,时代变了,观众审美趣味变了,如果戏曲再不变,遭到观众的抛弃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创立已有百年的日本宝冢团之所以历经一个世纪风采依旧,这和创始人小林一三定下的“以歌舞伎为基础,引进西洋歌剧和舞蹈,创立全新的国民戏剧”理念不无关系。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都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但创新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们能不能创立全新的中国戏曲呢,这是从业者应该认真思考的事!
源自:中国文化报